折扣爆料
折扣好货实时更新
前几天,跟片哥一起去吃河间驴肉,就在青山区恩施街,驴肉驴肠一拼盘,炒饼一盘,驴肉汤两碗,驴肉火烧一个,身在江城,却蓦然想起那些年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光。
1
还在杂志社做记者编辑时,常去北京出差,无非两个原因,一个是北京有记者站,起先在海淀黄村,后来搬到了朝阳路城市广场,公司买下了一栋写字楼的两层作为办公室,还可以住宿、做饭;另一个,北京的题材较多,跑跑公检法娱乐线出版社线,好采访组稿。武汉到北京,一趟高铁五个半小时,花费520元,成了我常来出差住宿的城市。
自己一个人,吃饭不方便,如果是朋友请客,一次两次尚可,多了呢,谁来出这份钱?于是乎,怕麻烦且社恐的我,认为一人食是最佳选择。当然,我也不会像现在博主“二百者也”这般,门门都敢进,毕竟帝都规矩多,不是还有一本书叫做《北京老规矩》么?很多时候,路边的小馆子,就是我的选择了。
一个城市的早上,人们会相互问候致意。武汉人会说,“过早木?”北京人会问,“吃了吗?您呐!”对,就像何勇在香港红磡演唱会问候香港人民一样,“我现在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,吃了吗?”这是真正的“民以食为天”,开口便是谈吃。
北京是美食荒漠吗?我个人以为,与其说是美食荒漠,不如说是每一种外来美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。北京太大,人口太多,只要味道好,总能赢得那么一群人的喜欢。
早餐店,我会从城市广场出来,小区门口有一家庆丰包子铺,炒肝、小米粥、包子;有时记者站人满了,我就住如家或者7天酒店,有些连锁酒店是靠近老小区,早点多,油条、小米粥、疙瘩丝儿,又成了我的早餐。
印象里,我没吃过焦圈儿配发绿的豆汁儿,而北京的小米粥比大米粥要多。南方来的人,会很惊讶,北方人喜欢喝大米或小米粥,但不喜欢吃米饭。但对我这个山东人,实在是太习惯了,京菜本身也是鲁菜进入北京后,与清真菜、宫廷菜结合为一体的产物。
在城市中穿行,尤其是逢上晚高峰或早高峰的地铁出行,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。有多次,我排队挤了几轮地铁,才挤上去。北京的生活,节奏异常高频,严酷难耐,而一个人的餐呢,的确很难自我伺候。大碗的兰州牛肉拉面、西安肉夹馍、北京炸酱面等,是一人食的重要选择。
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十里堡地铁站附近有一家河间驴肉火烧,大概有个150平方,我在那儿吃过几次,驴肉汤配两个火烧,可以吃到饱。远一点呢,可以在北京西站坐一站高铁到保定,吃吃驴肉火烧,凭吊一下陈年往事。
河间驴肉火烧,用的是渤海驴,是长方形,酱好的驴肉跟焖子一起,在掺杂青椒,塞到方饼。保定的驴肉火烧,用的是太行驴,是卤好的热驴肉,在圆砧板上快速剁碎,加上焖子,夹到圆饼中。圆饼要酥而脆,用刀一剖会听到清脆的破裂声,驴肉热而鲜,无上美味。我在保定基本上每餐都要吃两个火烧喝一碗汤。
说实话,我喜欢保定火烧胜过河间火烧,奈何北京多河间,少保定之味。是何缘故?有一个历史缘故,河间是冯国璋的故乡。
冯国璋是冯巩的太爷爷,是袁世凯之“北洋三杰”之“狗”(犬或豹,因太听话索性被人改为狗),在民国任过代总统,能打仗,指挥北洋军进击武昌起义的革*军,与黄兴相抗衡,放一把火烧过以大智门为中心的汉口,并连下攻下汉口与汉阳……因实在是太不解袁世凯风趣,有效忠清廷隆裕太后的嫌疑,结果段祺瑞顶替了其职位。
在保定,看看直隶总督府衙门,想想北方的“黄埔军校”保定陆军军官学校,保定这曾经辉煌百年的地方,如今随着京津唐的崛起,以及河北省会转到石家庄,都没落不堪了。
香河肉饼也是一个选择,人卫酒店吃过一次,精致小巧的肉饼,即决定寻一寻路边的味道,是在四惠东吧,靠近铁路的地方,有一个小房子,挂着香河肉饼的招牌,感觉就是山东大饼加了肉,只是要更细腻。
香河,是河北的一块飞地,位于京津中间,以家居和肉饼名。我有个武汉的餐饮朋友说,北京某某特别喜欢吃这个“肉夹馍”,会安排河北的人员半夜里给他快马加鞭地送。河北并没有什么特产肉夹馍,我怀疑要么是香河肉饼,要么是驴肉火烧,大抵后者居多。
北京有没有湖北美食呢?有的,但我并没有吃过。且不说亢龙太子曾折戟皇城脚下的烟云旧事,且不说早些年开在双井的热干面推车大叔,这两年一家叫做“过早MORNING”的小店曾爆红京圈,这是设计师、宜昌人陈铖所开,其红火还是因为陈坤的打卡,陈铖与陈坤的交集是因为一系列海报的设计。
名人带来的流量是锦上添花,陈铖的底子是最重要的。在采访中,他对我说,他曾在宜昌解放路一家开了许多年的热干面馆做学徒,放下所有,花了几个月,留在老师傅处习得手艺,后才有底气将湖北味道带到北京,如热干面、豆皮、醪糟蛋酒、藕汤、粉面、小面窝等,还北漂的湖北人一个乡愁。
故事说得好听,出品有颜值,故乡味道还原度有八成,设计感十足、窗明几净的原木色餐厅,飘着日式性冷淡气息,一双花臂大波浪发型自己出镜做模特给自家代言,你看不出这是一家湖北小吃店。陈铖告诉我,“我想做一家湖北小吃店,不一定要把黄鹤楼和长江大桥的图像搬进来,不需要墙壁上写满了湖北方言,有我自己的设计理念在里面,客人吃到这个味,找到久违的家乡,就够了。”当然,门店名“过早”本身就是能够凝聚湖北人乡愁的字眼,这是仅属于湖北人的早餐问候。
从东直门的30平小店到太平庄春秀路100平米,陈铖一反湖北早餐小店的常态,只做午市晚市,可以将一碗普通到极点的热干面卖到21元,三鲜豆皮30元,小面窝15元,人均消费48元,这样的价格,我们湖北的早餐从业者难以想象的事情,却在这个北漂的年轻人身上实现了。
2
一个人的北京,四处走走逛逛,京城太大,无人相识,乐得自在。
刚开始,我会首先去看北京故宫,人到北京,这个是选择嘛!逛了大半天,我也没看完,两腿走得发软,在后花园倒是休息得很舒坦。看着蓝天白云、红墙绿瓦,想到末代小皇帝溥仪呆在这院落里的确很寂寞,偌大的庭院,所有人都对之充满了阴谋阳谋,没一个说心底事的人,怪不得历代皇帝们会宠信太监或者外戚……忽而有导游操地道普通话,来到我前面,拿着一摞北京旅游团路线图问我,“北京X日游,只要XX钱,要不要,要不要?”……
有一年,因盗墓者意外打穿了棺椁的外椁板,南昌海昏侯墓的发掘势在必行,出土的墓葬,引发了全国的关注,名列当年考古界大发现之首。后来,在首都博物馆办过特展,我特意趁出差机会去一饱眼福,感觉整个展厅都是金光闪闪的金饼、金器,将海昏侯的宝贝,搬到帝都来展出,大有地方诸侯跟故宫天子叫板的架势,这是历代身居宫墙内的帝王所料想不到的。
北京的天桥特别多,天桥下有摆小摊的,卖水果买零食小吃甚至针头线脑的。阳光晴好的日子,目之所及,都是清亮亮的,天桥之上,看车水马龙,会分外有种孤独感。“北京太大了,拜访朋友一趟都要一两个小时,虽然同在一个城市,却也懒得前往……还不如自己静静呆着。”忘了是北京的哪个朋友跟我这样吐槽。
最常干的事儿,还是一个人没目的地闲逛。我会去北海,斗拱飞檐,廊腰缦回,宝塔巍巍,翠色连天,偶有民间手风琴歌手组合小唱几句,引来公园晒太阳大爷们的围观。从荷花市场那块进去,在老北京的胡同里穿来穿去,烟袋斜街、南锣鼓巷,像张北海小说里的某个路人角色,吃吃炸酱面,再去喝杯咖啡。那时候我还不怎么喝酒,要不然我定然会喝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(纯饮我还是搞不定)。
北京老胡同的每一座四合院,每一个院落门口的石狮子,大概都有那么一段长长的故事,有的是皇亲国戚的,有的是达官贵人,有的是悲喜交集,有的是红尘滚滚。至于恭亲王府,这座始于和珅的府邸,据周汝昌老先生考证说是《红楼梦》大观园的原型。
我也沿着护城河溜达溜达,人卫酒店附近的护城河两岸都是柳树,很安静,记得有一个小公园,有老人在里头吹洞箫还是笛子,白月光从柳树枝条漏下来,影影绰绰的。
在木樨路呢,盛开着粉色的大朵木樨花,再逛逛白云观,在附近的老小区边上转悠寻吃食,找到一家老北京爆肚,现在都忘了啥味儿了,只记得嚼起来很费牙。翻一翻那些写老北京爆肚的文章,我深度怀疑自己可能吃错了地方,要不然这样美好的食物,怎能过嘴就忘呢?
有次,为了去看颐和园,特意住在不远处的老旧小区酒店,冬天的夜里,吃了一碗朝鲜冷面,现在想起来都浑身发冷,至于我再也不想吃冷面了,实在是太冷了!圆明园呢,固然是为了看大水法的遗址,但无边的荷花荷叶是真的好看。如果说,南方的荷花荷叶是小家碧玉风范,北方的就是个性直爽的北京大妞,哪怕进了圆明园这种吸取了江南私家园林的风格,亦是如此。
像前些天“小阳春”的季节,很适合在钓鱼台国宾馆红墙外看银杏树。有一阵子,这里的几行银杏特别的红火,常有摄影爱好者持长枪短炮聚集于此。你想想两行高大的银杏树,树上是照得发亮的银杏叶,树下是黄叶满地,还有国宾馆红墙的衬托,再加一个古装美人翩然行过,镜头定格的一刹那,满城尽带黄金甲,能不美吗?那时候,还没有小红书,也没有抖音,我们也不太会P图,这里不需要任何P图与美颜。当然,香山红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但我印象中,似乎只去过西山森林公园,没有看到过红遍山的香山红叶,这是一个遗憾。
钓鱼台国宾馆附近有一个迷你公园,叫做玉渊潭公园。记得门票只要五元钱,还给一张类似于北京公交票的凭证,上面印着“玉渊潭”几个字。那是我在北京景点买票的最低价(要是论最低,可能是洪山宝塔寺,只要2元钱)。
3
多年前,有个朋友告诉我,她从北京机场下飞机,出来,外头是漫天大雪。身为南方人,靠前次看到这样的大雪,那一刻她爱上了这座城市。
如我这个朋友一般,北京这座城市,留下了太多的外乡人。和原大学同学一起在清华大学南门的街上吃烤鱼,跟原寝室的小山在家包饺子,两个人多少年都没有变,只是微微有点发福。
结识较多的还是记者朋友,新京报、法制日报、中国新闻周刊……大家像地下党一样,一有消息出来,即刻跟上,没有保留地交换彼此信息。那几年,是报业白银时代的晚期,后来则是黑铁时代。
出版社朋友也有不少,每当新书出来要做营销,他们总会发一批书目到我的邮箱,如果有感兴趣的书,即会向她们要样书。有些呢,不是给我送一本,而是一寄送有七八本,还有的呢,会在新年来临寄送来小礼物,来自北国的温馨。
记得和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约吃便饭,约在地铁站见面,她教会了我一个有趣的“拆新书”方式,两只手捏起书的两侧,掌心向内,顺势一合到低,包裹书的塑料薄膜即会就此崩裂,那是作家虹影的英国爱人亚当•威廉姆斯(中文名韦蔼德,英国怡和洋行驻中国大陆首席代表)刚出的新书《乾隆的骨头》(他还有一部书叫做《慈禧的面子》)。我有一个同事特别喜欢虹影,跟我讲,“记得跟我要签名啊!”
那一次在酒仙桥虹影家采访,我特意跟她要了签名,虹影将名字书写在《饥饿的女儿》上,亚当•威廉姆斯则在《乾隆的骨头》上签名,我一下子有了这对爱人的签名。因为采访需要,虹影的女儿波妞给我和虹影拍了合影,她的小手晃动咔嚓一下,我回去发现,这是一张模糊的照片,一个出自混血女童之手的杰作。
虹影,出自“火锅之城”的重庆姑娘,身材娇小,本名陈红英,网名叫“火狐虹影”。火狐,与如今珞珈山上罗曼蒂克的白狐不同,是一种昼伏夜出的狡猾动物,不被人豢养,生性多疑,但多灵性,爱自由,这多多少少跟虹影的出身与个性相关。在离开上一段跟赵毅衡的“波伏娃与萨特”式的感情,选择亚当•威廉姆斯时,她在梦中听见母亲对她说,“这一次,我只想找个爱人,而不是一个父亲”。这个人果然成了与她育有子女的爱人。
我在北京又遇到了黄勇,那个在集家嘴码头附近嚷着说,“我要撒尿入长江,随着那大江滚滚东去……”这是一个难以诞生英雄的时代,我们只能以一些看似荒唐的行为来表露自我。
黄先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乐队,还自费出了一本诗歌小集。他起初是一家著名教育出版社的编辑,后来因拯救流浪猫狗计划入狱,出狱后,辞去工作,改行做漂无定所的音乐人。
我参加了他组织的天台游园歌会,他操起吉他,对着北京的天空唱歌。“如果凌晨起来,你会看到北京的大楼下闪动着火红色一闪一闪的烟头,像繁星开满了大地,那是在冥思苦想文案计划的广告人。”他跟我说。他的比喻像王家卫的电影,带着朦胧的诗意,带着被打散的人生重构。
有一位著名电影里的小角色演员,转行做导演与制片人,因缘际会,始终没有成功,我们有过多次交集。她喜欢罗启锐作词、李宗盛作曲、蔡琴演唱的老歌《给电影人的情书》,在片场,在车上,或者是休息之时,她的手机总会播放这首歌,“你苦苦地追求永恒/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/你傻傻地追求完美/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/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/何必笑骂恨与爱/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……”再后来,我在微信上接到了她因癌症去世的消息,人生的后半段,她留下了太多人的不解、非议和误会,而她的电影始终胎死腹中。
后来,中国好声音冠军单依纯也唱过蔡琴的这首歌,还将自己唱哭了。我以为单依纯还是太小了,唱不出蔡琴那种经历世事、哀而不伤的沧桑味道。大悲无言,泰山崩裂于眼前,也要毫无情绪,面不改色。
再后来,时间来到了2019年元月,我离开了杂志社,这年底小口罩爆发,我再也没去过北京。北京的这些往事,如今想来已是恍如隔世,我们终究是回不了。
武汉的深夜,我翻看《午夜北平》,看外国人笔下的老北京离奇凶杀案,唐鲁孙梁实秋邓云乡张北海等人书写北平之美,《茶馆》里“我爱大清国,我怕它完了”……我想起一个武汉好友的北京往事,他是一个摄影师,刚到这个城市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住过地下室,邂逅过美妙的爱情,在北方时拍下来许多名人明星,为了家人于武汉定居,但他还是很想念北京,这一个五彩缤纷的都市。
年少的时候,在选择城市读书生活时,我首先排除了北京,以为生活节奏太快,太多的北方年轻人将迈出本土生活的首座城市定位北京了,我想选择相对安静的城市,过不一样的生活。误打误撞的是,工作后却跟这座城市有许多的交集,到现在也忘不了,这也是彼时难以预料的。
回到1994年,在“**主义”灯红酒绿的香港,生在刚启蒙不久北京的何勇,他的《钟鼓楼》呐喊道,“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。”那一刻,一旁的三弦演奏者是他的父亲何玉生,穿着中式长衫,微闭着眼睛,以从头到尾的中式传统与大陆摇滚最辉煌时代融为了一体。多年后,何勇发疯,何玉生在接受采访时候表示,即使时光倒流,他也不会阻止儿子走上摇滚路。“人真奇怪,除了吃饭,还要思想自由。”他这样总结道。
作者:舒怀
图片:网络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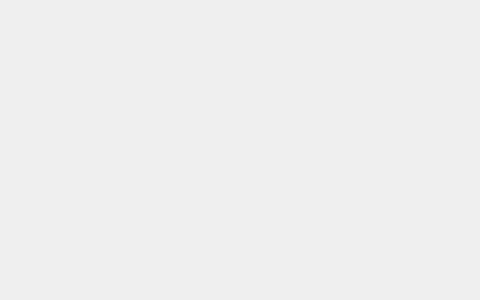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8677
8677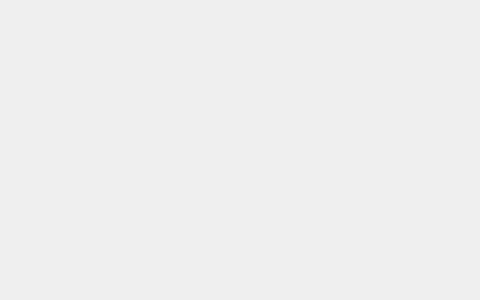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9238
9238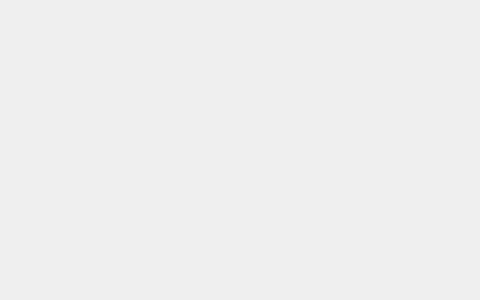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8500
8500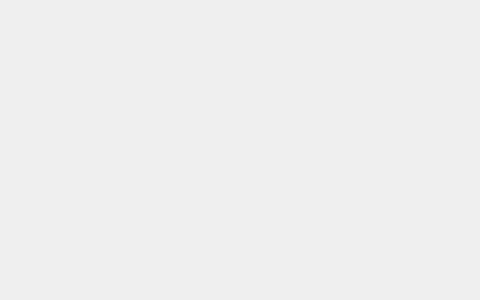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9196
9196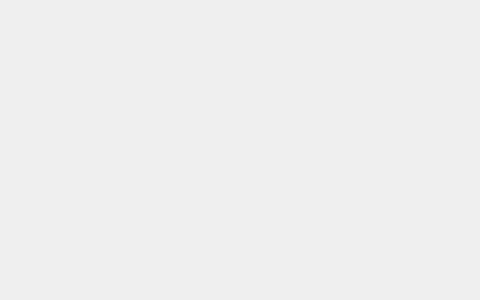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8753
8753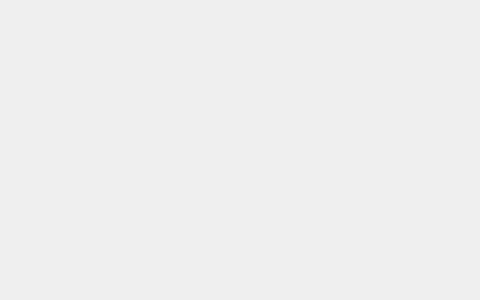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9750
9750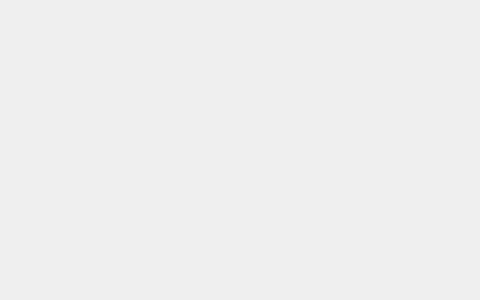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9646
9646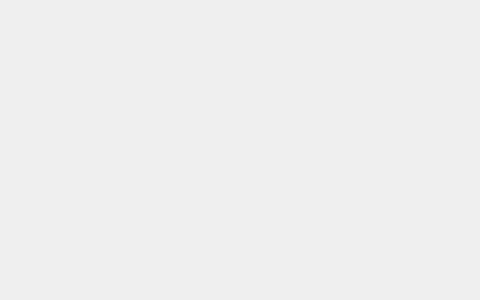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10099
10099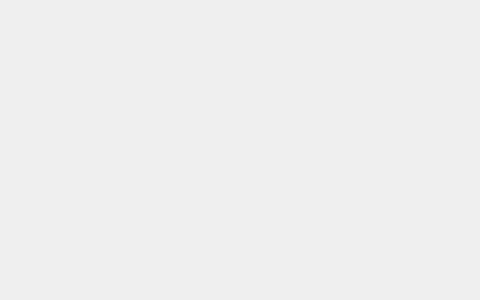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9456
9456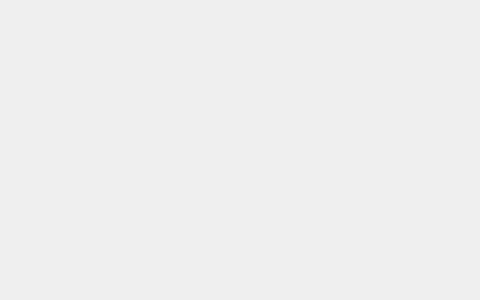
 8177
8177折扣好货实时更新
达人好物推荐
参阅喜友买家评论
晒图分享制作攻略
 大武汉美食榜
大武汉美食榜